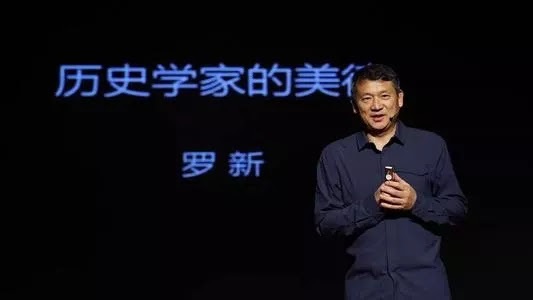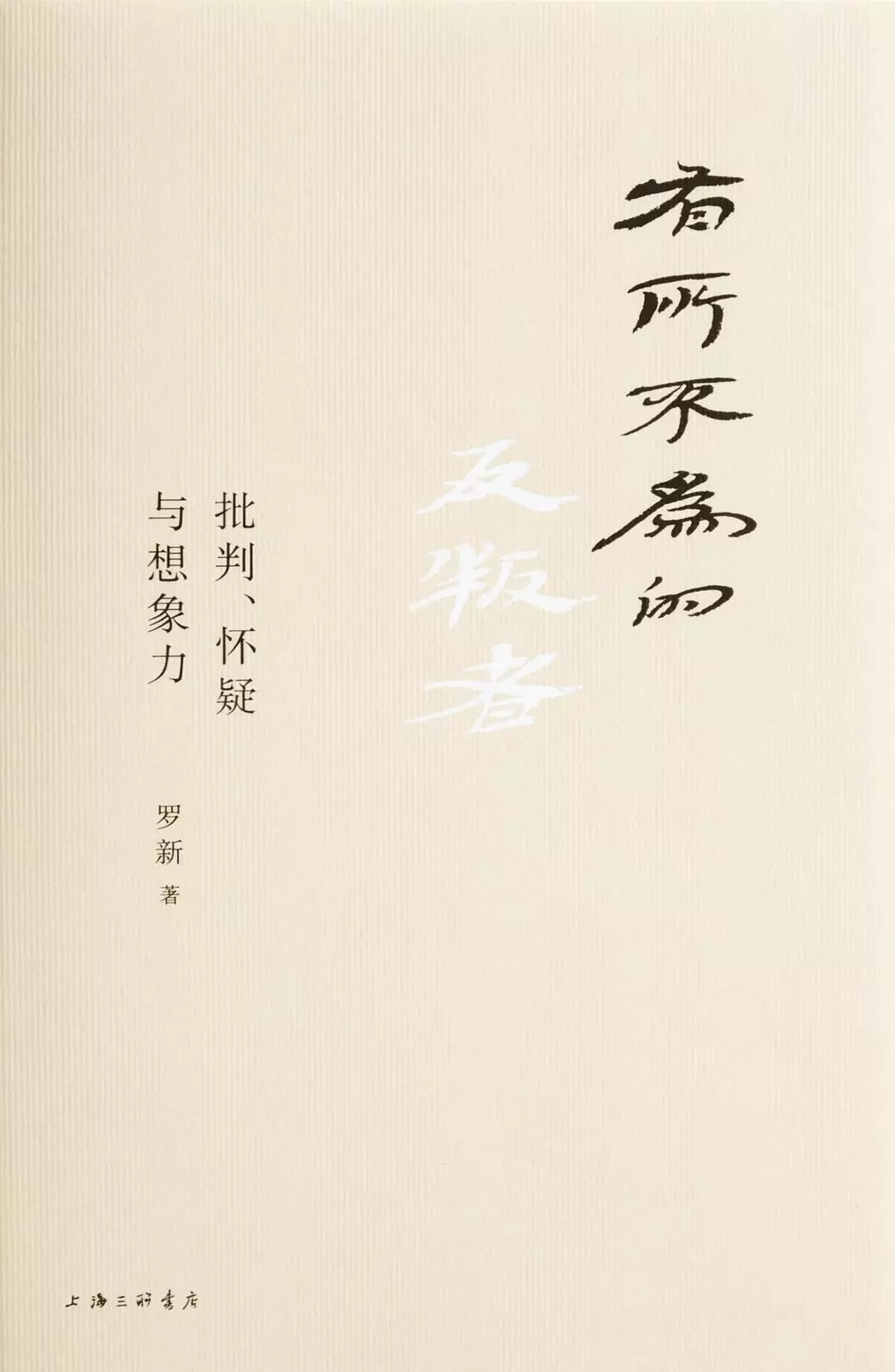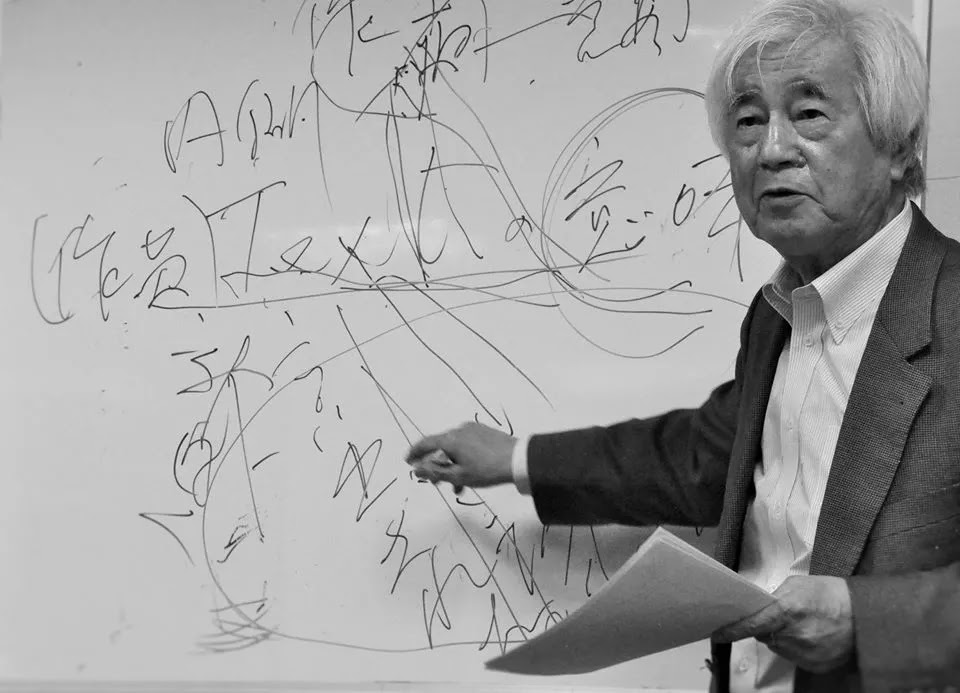作者:微信 明清书话 转载自:议报
罗新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著有:《杀人石猜想》《中古北族名号考》《历史的高原游牧》《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等。
面对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沉渣泛起,罗新反思了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
他举例道,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借一己之力制造出来的,历史知识也是制造他背后的种族主义等思潮的原料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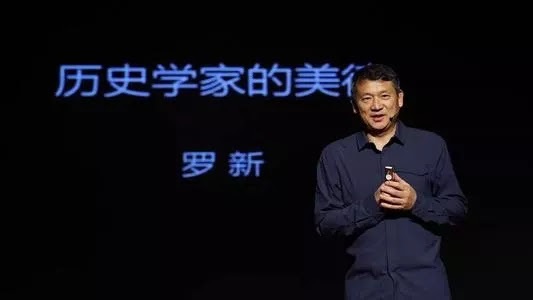
与之相似,今天大量“网络民族主义者”的激烈言辞也源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者常识。
因此他认为,历史学要对自己时代的历史负责任,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
不能为了现实的、具体的、短暂的目的去编造历史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批判传统历史学的“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能否讲一讲“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罗新:历史讨论时间问题,总要追溯到时间的源头。任何问题、任何事件、任何人群,都要说到起源。
里尔克有一首诗,讲一个平凡旗手的死亡,他说:“一刹那把另一刹那抛弃了。”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时刻都是在起源,每一个时刻也是在终结。
我们在叙述里特别喜欢寻找遥远的起源,并且喜欢把遥远的起源和后来特别是现在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用起源来解释我们现在的状态。这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的思维的方式。比如说一个人很高,我们就会推测他的父母很高,进一步推测他祖先很高,可是这中间其实有无数的变化的可能。其实,起源和今天没有关系。
另一个是迁徙崇拜。在讨论人群历史比如说民族历史的时候,迁徙崇拜认为,一拨人会完整不动地经过长途迁徙来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不可能的。
迁徙的过程当然有,但是这个过程在经过变化,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加入,旧元素消失,新因素出现,才会有今天。
我们在今天还在迁徙,这么多北京人哪里来的?几十年前北京才几十万人,现在几千万人,当然是迁徙的成果。又比如说,今天我们不能说美国人都是从英国五月花号的后代,五月花号的后代现在还有多少我都很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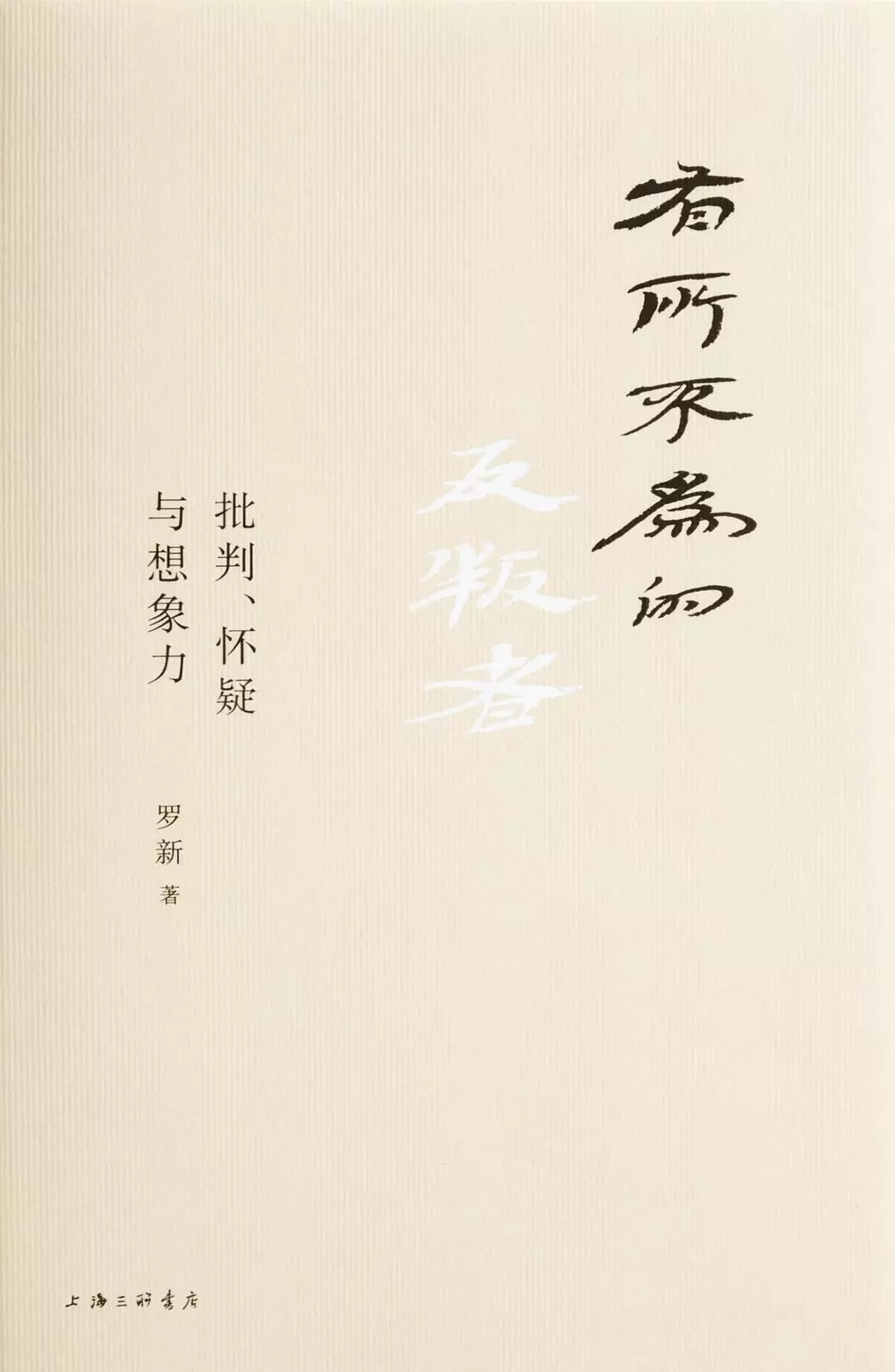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罗新 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5
界面文化:为什么人们要强调这些?
罗新:因为这样可以强调一个民族血统的纯正、高贵和遥远。
比如说,希特勒说日耳曼人是古老的雅利安人的后代。其实不管有没有雅利安人或者日耳曼人,古代任何人群都在不停地和其他人群进行基因交换、文化交换等各种交换。
有旧成员的离开和新成员的进入,人群和人群之间剧烈的交换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人群和人群之间不可能存在清晰的边界。
但是我们在叙述的时候总是强调有边界。
一是强调时间上的起源,一是强调空间上的迁徙;不管时空相隔有多大,人们还会相信一群人可以完整地成为今天的另一群人,或者可以用那样的时间空间上的另一群人解释当前的这一群人——历史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想强调,现实生活中没有古老的人群,所有的人群都是崭新的。今天我们是一群人,明天我们会分散,变成新的人群。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到近代社会才形成的民族。

界面文化:现在有些学者也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转而尝试探索亚洲的新的可能性,比如说在沟口雄三、子安宣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怀,他们某种意义上都在寻找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可能。能否谈一谈你对此的观点?
罗新:我不是说共同身份的建立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做到,我是说,不能够因为要建立它而开始特意讲述相关历史,选出历史当中对此有利的而去讲述。比如在东亚有共同的命运。我们看到东亚自古以来就有内部斗争,而且越往现代越血腥、分离得越深刻。如果只讲中国和日本只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把血腥历史淡化或者故意不讲,那也不是历史。
不能为了眼前的目的去讲历史,历史就是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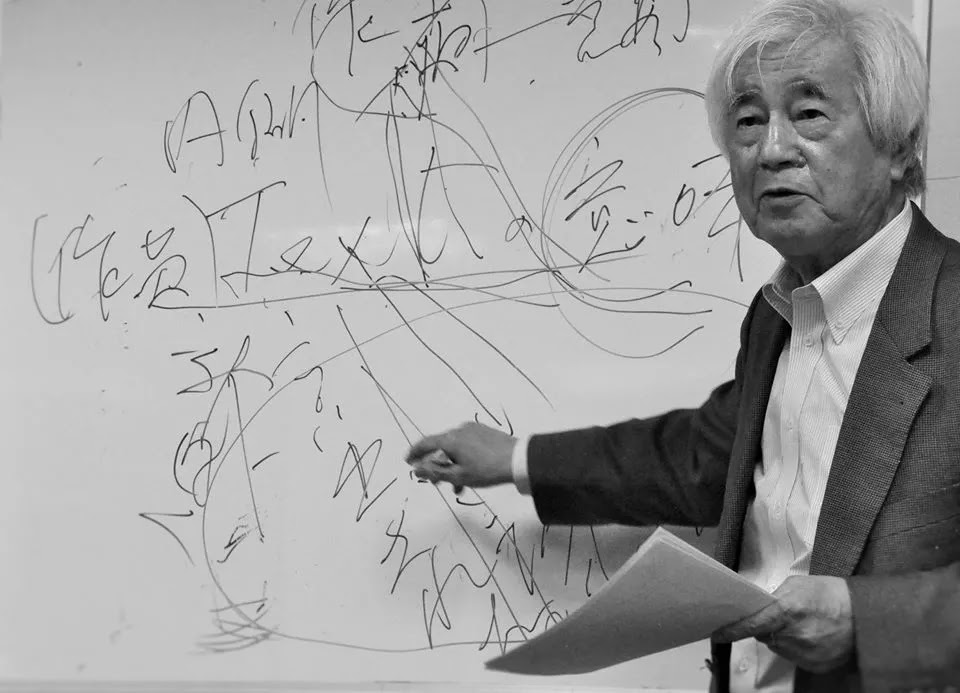
子安宣邦,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界面文化:建立东亚共同体有可能是基于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能否请你讲一讲政治体和文化体的概念?
罗新:政治体指政治构造。中华民族当然是一个政治体,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群合起来叫中华民族,也就是说划定边界不是因为人们都说共同的语言或者相貌和别人有明显差别。
例如,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可是在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就不是中华民族。造成这种差别的是国家。
国家是政治体,所以我们说民族都是政治体。甚至连今天我们以为是族群意义上的、有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汉族,在形成的早期也都是政治体,是一股政治力量,比如说因为秦汉时代的政治发展促成了境内的这群人逐渐变成了互相认同的、文化上有很大一致性的人群。
文化体是有某种共同文化的,说同样的语言、有共同的风俗、有共享的历史。很大意义上,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和中国境外的蒙古族是一个文化体,但不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政治体和文化体的区别。
儒家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为东亚地区很多的人群、许多强大的王朝共享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是否足以说明共享这个文化的人群之间必然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当然不是。
界面文化:那么,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之后,我们要走向哪里呢?
罗新:不为了现实的、具体的、短暂的目的去编造历史,不从历史中抽取某些事实组成新的讲述方式。
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讲自己想要讲的历史——你可以讲东亚有某种共享的文化,但是另一个人也可以讲东亚近代以来巨大的分裂和对抗——都可以讲,各讲各的。

界面文化:在你的书中我们还看到新技术的发展对民族主义的促进作用。比如说互联网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很多人却成为了“网络民族主义者”。
罗新:过去,民族主义者在现实中进行表达,通过出版著作、喊口号、贴标语,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提出抗日主张,都是民族主义的行为。
但是今天的网络民族主义不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言论和行为(来表达),而是通过网络发言。这种发言在某种层面上是安全的,不需要负责的。
因此有时候会表现出更加随意和激烈的一面,激烈到侮辱谩骂的程度。
互联网时代民族主义达到了很猖獗的程度,这是让人意外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政党、政权用某种行政力量来组织的民族主义,而是许许多多的个体在网上互相激励、互相交流而走到一起去,形成了巨大的网络力量甚至是网络暴力力量。这个现象在所有的人群中都存在,不只是在中国。
界面文化:你有想过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吗?
罗新: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在人群的内心有很深的基础。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稳定以后,由政权主导的媒体、行政组织没有鼓励民族主义,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在控制这些行为的发展,我们觉得(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不存在了。
但是网络使得另一个空间出现了,非政府的力量出现了,过去这些力量在生活中是非常碎片的,可是他们却在网络上集聚起来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
现在民间的民族主义的激烈情绪,可能不只是人们对民族问题、对国家问题、对某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思考。
我非常想强调,网络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声音在别的方面得不到倾听,利益得不到代表,只是找到了自己认为是安全的发泄口。
他们无法表达对很多问题的感受,因此就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毕竟骂外国的表达相对安全。
再比如有些人在提到对穆斯林的情绪的时候,发言显得非理性,但是也许这种情绪背后是人们对其他方面的情绪酝酿,比如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升学没有分数照顾等等。
也许在更大的网络空间里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很久,到这个点上,某些言论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可是非理性的东西也有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