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章润 转载自:网络
曾几何时,年龄与学生相仿。有的同学齿德稍长,社会阅历更多。在师生分际的有限礼仪之下,彼此实际分享的是兄弟情谊,张口喊饭,一笑出门。皆贫,身无分文;都天真,心怀天下。多少个时辰,议酣血热,推杯换盏,称兄道弟,风斜河汉天香夜,精神如画。
它们构成了我青春记忆中的一抹彩色,说的是那一种叫做“八十年代”的故事,山远水长。存在长存,万物皆流,流水般的师生来来去去。

一转眼,不觉不晓,成了他们的父辈。突然,有些不适应,怅然若失,欣慰而又张惶。“做人”,这个艰辛而庄敬的字眼,老话,大白话,原来意味着需要以毕生长旅为代价,一步一步往前跋涉,如夫子所言,始能徐徐知之也。
熬到父辈,未必收获到了更多的尊敬,但因代际距离,却有了远远审视的便利。他们还是那般可爱,一如我们曾经在自己的老师眼里的模样,也就如我们的老师在他们的老师心中的记忆。然而,隐隐的,痛痛地,觉得下面要说的这类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名校尤然。
这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略去枝节,概莫如此这般。
首先,他们聪明,但无才华。会考试,什么样的答案能得高分,就造出什么样的答案来,一点就通。答案之外,多读无用,懒得溜一眼。细数下来,高分学生,“三好生”,多半读书甚少,好像也基本不读与分数无关的书籍,蔚为学府新景象。
会参赛,这个“杯”那个“杯”的赛事啦,培训复加演练,按照要求做就是了,至于有理没理,有趣无趣,何必想那么多,不就是要一个免试入读研究生的资格而已。——也许,有用就是有趣,有用等于有理。
需要什么证书吗?行呀,考一个,至于自己喜欢不喜欢,有意思没意思,另当别论。瞧,“七一”、“十一”的歌台上,就数他与她的声音嘹亮呢,那声音可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哟!
十多年的应试教育和威权主义生活氛围早已教会他们,按照标准答案行事,不仅可以免去面对未知世界的迷茫,而且,一定引导向成功。执着于面对迷茫的,可能反而遭到淘汰。——我们这些父辈,该当何罪?
其次,他们应变,却不见性情。小小年纪,就人情练达,识时务,似乎从稚童一步进入成熟的中年,将那个充盈千万种奇思妙想、热血沸腾、叫做青春期的生命时段压根儿删去。世事洞明,懂得结交“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精于计算哪门课、哪件事有助于“成功”。
党团活动,讲一口字正腔圆的;社团活动,来一段热情洋溢的;碰上教授,或许发表点愤愤的;领导面前,即刻大方而娇羞,单纯无辜却又知情达理。可他或者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似乎永远躲在多彩多姿却又不动声色的面庞之后。如今电视中天天出演新闻的那些面孔,不少就是这副德行。
再次,他们有志向,可理想贫乏。志向就是“成功”,直截了当。或者,换一个表述,“卓越”。再直白而浅显的,叫做“做大做强”。就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多数时候其实不外权钱二字,以及其他可得藉此一般等价物置换的浮世物件。
但是,个人志向无涉公共关怀,亦无家国之思,终究苍白。我们读何秉棣先生的回忆录,翻来覆去的不过就是“出国留学”、“争当第一”这类呜呜呀呀,感觉上甚至不如读杨振宁先生的回忆来得亲切感人,难以生出同情来,原因就在于志向与理想的层阶不同。其志固大,而精神境界渺矣!其业不凡,而人格气象隳矣!

最后,他们敢想敢干,实际上并无血性。万物皆役于我,这是最敢想的,也是想当然的。似乎屡考屡中的少年得志,更加使得此一虚矫云山雾罩。由此,自私,极度的自私,不是多吃多占式的自私,而是惟我独尊、为了成功不惜一切的虚矫,竟会成为他们的显著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
会动手,善执行;从来不曾、永远不会热血沸腾。看看今日中国问题成堆,而独缺政治决断,表象为温吞,囿于既得利益,实则不敢担当,了无血性,早不复见邓公当年之气吞山河,便可见共和国教育有病,迁延发作罢了。
毕业后,约摸十几、二十来年,他们就会出头,一些人甚至光艳艳,亮灿灿。如今现成的两个词,好像是专为他们打造的。
在一种场合,笼而统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叫“成功人士”;在另一些场合,直指要害政治学上的定位,称为“技术官僚”,或者,马克斯•韦伯的用语:“专家”。

他们是正常人,太正常了,连自己都容不得自己有一些儿出格。他们明白时代风气的需要、自己的实用价值和努力方向,也太过明白了,太早就明白了。他们奉守成功哲学,孜孜于此,一切围绕于此,也多半会走向梦寐以求的成功。
原来,人在所谓的智商和情商之外,尚有义商、仪商和灵商,如果“商”在此能够作为一种衡量单位的话。有的人,天性厚道,具有较高的良知感和道义精神。即便经磨历劫,老江湖,心底的良善不泯。
有时,它表现为一种拍案而起、见义勇为的牺牲精神,困勉以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悯。而这一切跟所谓的教育无关,通常为心性使然,人之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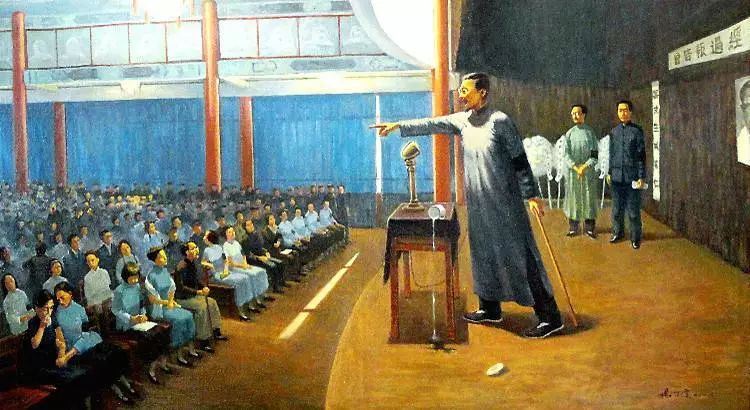
相较而言,也有人天生就是坏坯子,教育不管用,惩戒可能反会促其变本加厉。想一想史铁生笔下的K吧,十一二岁的少年,“他那恶毒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还有的人,更多的人,在此两端游移。
或者,由好人变成坏人,自坏人转为好人。于此一事,良善油然不能自已;在彼一端,不掩性恶昭彰。其间的差别,不在智力,亦不在情商,而在良知感和道义精神之高低有别,姑谓“义商”。
一些人,天性温良,敦厚有礼,相与情厚。可能,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也有些人,天性粗陋,哪怕身居院士,却终究不脱戾气,甚至一身匪气。那叫做“新工人”及其后继者之“新新工人”的,将无礼当作犀利,以无聊为幽默,更是不堪。
曾有年轻人问:某某在西方那么多年,怎么坐没个坐相,站没个站相,吃起来更是一脸龌龊?西人并非天性人人温文,自不待言,所谓的礼仪更是需要三代磨练,可他或者她虽历芝兰之室,却了无馨香,这便说明教养有憾,缺了“仪商”。
我们心性中还有一种情愫,表现为对于庄严的敬意,关于神圣的憧憬,凸显着人类用思想来思想,以生命印证生命的伟大禀赋。它们提澌着我们对于生命之为一种存在的思考,并可能导向信仰之境。无以名之,姑谓“灵商”。
这种情愫,在有的人心中较为充沛,将终极关怀萦念于怀。在有的人心中则为各种业障所蔽,湮没不彰。智商虽高,而情商有限,灵商湮灭,是这个世俗化时代的人类特征,更显得此种情愫之难能可贵。
凡此五商,智商、情商、义商、仪商和灵商,久经修炼,积存心性,出诸举止,即所谓的理性、良知与教养。它们合共于一身,构成了一种君子人格与超越心性,是谓读书人所当修炼的功夫,必须臻达的境界。

我们看看梁漱溟先生,布衣素衫,而气度自在,就在于梁先生修炼出此种人格、心性、功夫与境界。否则,可能“成功”,却难言卓越。——卓越,一定意味着人格的完满和心性的丰盈,否则,只能说是“成功”,甚至于麦道夫式的成功。
看看如今的世界,不分东西,从华尔街、陆家嘴到清华园,横行霸道的是“无灵魂的成功”与“无教养的成功”,可见不仅人类未必真的一直是在进步,即便确乎持续进步,也未必就能致达至善之境,更非完满之境。
不,照此路子走下去,绝对无法通达此境。
也许,所谓至善和完满,都是不可实现的梦,道德理想主义的上帝之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和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与应对,而无不为此所苦恼,正说明其路漫漫,知无涯,思无涯。
其实,当年茨威格环顾诗坛,就曾感喟,回想起曾如星汉照耀过自己青年时代的那些可亲可敬的名字时,心中不禁疑惑:“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生活方式呢?
茨威格说,在这个时代,常年充斥耳膜的不是宣传机器的聒噪就是战争的隆隆炮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
可能,这一生活方式终于在神州登场了,而且,来势凶猛,变本加厉。
每念至此,无地彷徨,去找自己的老师,诉说流水帐,絮叨茶杯里的风波。老人家点头又摇头,摇头复点头,一阵忙乱,几场咳嗽。末了,终于平静下来,转过头来,缓缓道来:
“你觉着奇怪吗?”
是呀,看官,你难道觉着有什么奇怪的吗!
可是,我这个教书匠,真的觉着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了。莫非,时移世易,我已成了九斤老太?而身役教书匠,最为惆怅的,莫过于和自己的学生之间有了隔阂。或者,与这个当下时代风气不和。于是,不进则退,自作多情?
又或,“老境何所似,只与少年同”?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