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迪 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
题图:2022年8月26日,年轻人在北京参加招聘会。(法新社)
本周二,著名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而轻生去世的消息震惊各界。精神抑郁问题近年来在中国日益严重,尤其是年轻人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年龄人群。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7月5日晚,香港著名女歌手、年仅48岁的李玟突然传出去世的消息。她的姐姐李思林在微博发文披露,李玟数年前患上抑郁症,7月2日在家中轻生,经抢救无效,7月5日去世。这一消息不仅登上各大中文媒体的新闻版面,也再次引发人们对于抑郁症这一现象的关注。
报告:中国年轻人是精神抑郁高风险群体
过去20年间,中国的精神障碍和抑郁症发病率呈爆发式增长,患者年龄也在明显下降。今年2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0.6%。其中,青年为抑郁高风险群体,18岁至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25岁至3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2.3%,也显著高于35岁及以上各年龄组。与此同时,精神焦虑风险检出率的年龄差异也呈现类似趋势。
报告显示,所谓“抑郁风险”并非经过专业医师诊断的“抑郁症”,而是指使用标准的心理测验方式测出受访者在抑郁量表上的得分,其分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存在抑郁症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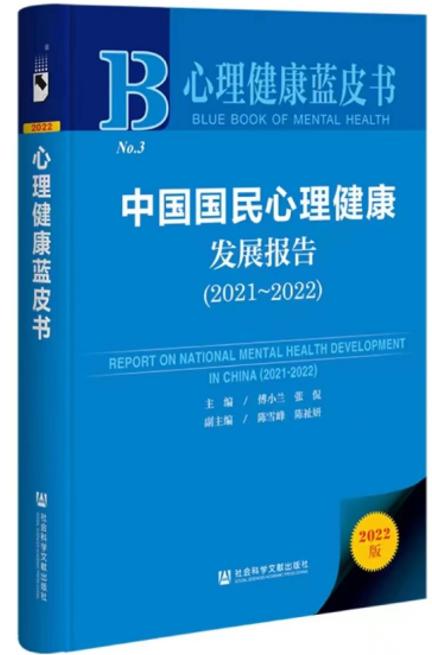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封面截图
那么,青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又会对社会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告诉本台:“这一代其实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是事业的上升黄金期,对社会开始做出贡献的时候。但是,如果整个群体(心理)出现巨大问题的话,可以想象那就象一个炸药库一样,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爆发。”
关注人权的女青年:恐惧但又不被理解
谈到精神抑郁的问题,住在北京一间出租房、处于半失业状态的王霞告诉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昨天下午差一点就跳楼了。”
王霞大学毕业3、4年,最近这次抑郁症的发作是由于她和母亲在电话上吵架。她说:“我接电话的时候对她(母亲)哭了很久,而且大喊大叫,然后我就到阳台上推开了窗户,当时我想跳楼,但是我男朋友很快就从后面把我抱住了。”
王霞已经和母亲争吵多日,直接原因是她认为母亲过于强势又对她不能理解:“因为我家有太多完全不想让她看见的东西。”她说,“不想让母亲看见的东西”就是家里收藏的与国内人权抗争者相关的纪念品。
从大学时代开始,王霞就关注中国人权议题。毕业后,她离开家乡到北京打工并继续参与人权及公益活动。最近两年,中国的人权法制状况急速倒退,但王霞依然克服内心恐惧,多次参与援助异议人士和青年行动者,包括呼吁营救去年“白纸运动”的被捕人士。虽然并没有做什么“大事”,但她的内心还是经历了很多创伤, 并因此产生了焦虑和抑郁的症状。
她说:“有一次,我去探望了一位遇到麻烦的朋友的家属,当时我被国保发现了,被拦截了一、两个小时。之后那天晚上,我开始失眠。后来大概有一周时间,我都很难集中精力工作,一直都在喝酒。”
不过,对于这些内心的痛苦和压力,王霞却无法透过向家人诉说来纾解。她说:“我父母都是体制内的人,而且我母亲控制欲非常强。她非常喜欢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也对我的价值观非常轻蔑。这种感觉让我感到又恶心又恐惧。”
中国的心理咨询服务价格昂贵,很多所谓的医师也不具备合格资质,王霞也很难评估咨询这种“政治性抑郁”的风险。因此,她至今无法得到良好的心理咨询治疗。此外,工作不稳定和收入的微薄,也更让她有着严重的不安全感。她目前只能不时地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幸好有男友时常陪伴,给她以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被校方“上岗”的大学生
王霞的男友小孙目前还在大学读书。他们在一个讨论政治的群组里相识,并因三观相近而走到一起。不过在校内,小孙也是被校方严密监控和打压的对象。
小孙说,他最初是因为拒绝按照校方要求安装“国家反诈中心”应用程序,反对该程序搜集用户个人信息,而成了校领导眼里的“异议分子”:“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太过分的对抗,我也没有号召其他人跟我一起抵制。我只是一个人不装,也很低调,但是我的辅导员约谈了我。他那次态度其实还挺恶劣的,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
2022年疫情期间,小孙所在大学从8月开学直到“白纸运动”爆发,整整4个月都处于封控状态。但校方对学生的所有封控规定都是由老师口头传达,没有文字,学生们很不满,但也难以投诉。小孙便向校党委办公室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布防疫封校的有关政策文件。当时,他还咨询了一位维权律师,没想到他们的微信私聊被国保发现。
小孙说:“国保直接找到我们学校保卫处,要求调查我。我就连续被约谈,我们校长亲自在管我这个事情。他给我们学院施压,说我们学院育人出了问题,要他们整我。”
巨大压力下,小孙不得不放弃信息公开的申请。后来,辅导员还专门安排同宿舍内一位已入党的同学对他进行监控,随时汇报他的动态。这让他感到非常烦恼,而陷入焦虑状态:“我会清楚随时都会有人在盯着我,我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任何安全感。”
另一个让小孙感到焦虑的原因则是每个中国大学生都在面对的巨大升学和就业压力:“入学第一天的时候,院长给我们新生讲话。他就说,你们这个专业毕业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只有考研一条路。考研率又那么低,所以大家都基本很绝望的样子。”
体制内女青年的职场梦魇
不仅是身在大学的学生感到压抑、绝望,就是已顺利就业的年轻人也感到扭曲的社会现状令他们难以适应。身在小城市的刘方,大学毕业刚在体制内工作4年就被确诊患上抑郁症。她认为,这首先是因为自己坚持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环境格格不入。
刘方说:“如果用他们批评我的话就是,我比较‘崇洋媚外’,思想比较西化。我是比较信奉那种普世价值,就是自由平等民权(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性格刚直的刘方在工作上不喜欢盲从,更不屑拍上级马屁。她说,因此就受到了直属上司的排挤打压:“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皇上一样,底下的人要揣摩上意,但我恰恰是不会这么做的人。他发泄的行为就是不停地给我的工作挑刺,比如说我犯了一个很小的标点符号或者是页码的错误,他就会说,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玩的。每周开例会的时候就会把我拎出来,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而且就是这种PUA(指精神控制)的骂。”
刘方说,除了被公开羞辱,上司还对她有一些性骚扰的行为,但都被她直接拒绝。这令上司对她更加不满。刘方形容,自己这几年来受到的精神虐待“就像是一场恶梦一样”,但是由于经济不断下行,她没有把握辞职之后能再找到工作,因此只得忍耐。
与此同时,刘方也感到整个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还在加剧,包括“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等伤害女性的社会热点新闻,都对崇尚女权的刘方内心造成巨大冲击:“无怪说很多人都讲,在中国,结婚证就是一张卖身契。因为一个男的他只要跟你结婚了,他就可以打你、骂你、奴役你,然后抢夺你的生育成果、劳动成果。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法律都在支持他。”
因对社会感到失望,刘方一直不肯谈恋爱、结婚生子,并因此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今年3月,医生确诊她患上了抑郁症。
疫情后 人们变得更抑郁了?
过去三年,中国当局各种严厉的疫情封控措施,对民众心理健康也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有调查显示,去年上海封城期间,超过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现出抑郁情绪,求助心理热线的人数爆增。
那么疫情过后,人们的心理状况是否已经好转了呢?
“这么说吧,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们开心。”身在上海、现年30多岁的赵迪对本台记者说,现在国内无论是民企、国企还是外企都遇到了很大危机,大量裁员很普遍:“就这三年,把所有人的梦想都击碎了。大家都感觉自己跌入了谷底,好一点的就躺平,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你背着几百万的房贷,就会有种生不如死或者说每一天都心惊胆战的感觉。”
长期在外企工作的赵迪说,作为中国经济重要对外窗口的上海,仅她知道的港澳台及西方外企,近两年几乎走了一半甚至70%。今年前4个月,经济稍有复苏,但五一长假后却又是断崖式的恶化。她解释说:“很多人发现这几个月也没有变好,那我就赶紧撤,保命要紧。这样一来,我觉得(经济)短期内、几年之内是很难很难恢复的,因为信心的恢复、重建,这个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
伴随经济大环境的恶化,令赵迪感到更压抑的是言论空间也在明显缩小,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她说:“有时候,我甚至看到网上一些网友因为谈论自己失业了、没有拿到赔偿金或者说要考虑去仲裁,就被判定为‘负能量’或者说是‘不和谐的声音’就被封号,真的很莫名其妙。”
赵迪表示,现在不仅身边的朋友几乎人人都被封过号,很多她曾在微博、知乎上关注的网络大V们也从疫情开始后,纷纷因为踩到了某些舆论“红线”而被噤声。
“当我们主要的一种沟通渠道被切断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很憋,就像被捂住嘴一样,然后这种情愫就会在心里发酵。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陷入了一种普遍性的抑郁。”赵迪说。
“这个社会已经病了”
曾在中国专门从事过青少年心理救援项目的任瑞红告诉本台,现在中国年轻人心理问题突出的原因,主要就是源于社会环境的生存高压和不稳定。
“中国现在整个大环境,我们都知道经济压力很大,社会保障严重不足,每个人都处在一种担忧的状态下……。很多这一代人是关心政治的,尤其是大城市的,以前他们还可以翻个墙、上个网,发发牢骚,现在肯定是不敢的。” 任瑞红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在各种压力下已经被挤压得变形,既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情绪出口。
“大部分人的承受力不可能是那么好的,当达到了极致的时候,这种负面情绪就会在整个社会蔓延爆发,(形成)一个社会性的抑郁。” 任瑞红说。
前文提到的刘方也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打开社交媒体,每个人都在发泄自己的负能量,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某种疯狂的想法:“这种心理的疾病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已经是一个群体性的创伤了。”
赵迪则坦言:“我一直觉得这个社会已经病了,病到如今这种地步也不是靠一贴药或几个医生就能医好的。”她认为,中国社会走到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做一个好人。“我觉得每个人能够做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不要再去做恶。争取做一个好人,那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慢慢变好。”
(出于安全考量,本文中的青年受访者王霞、小孙、刘方和赵迪均为化名。)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23.7.6.






